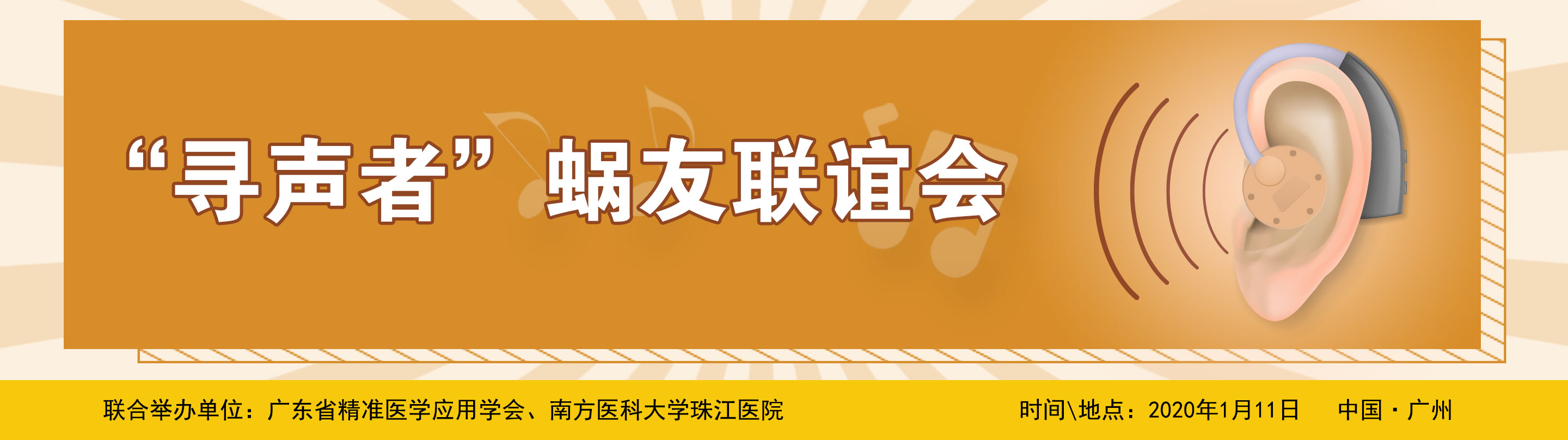这场特别的聚会,来了一百多名“寻声者”,分享重返有声世界的历程,连医生本人都感动泪目。
“我工作赚钱最大的动力,就是为我妈妈找回声音,让她有生之年能够听到我喊一声‘妈妈’。”52岁失聪40年的叶阿姨,她的儿子小陈说出了自己30年来的心愿,如今他已得偿所愿。和叶阿姨一样找回声音的,还有15岁的学霸少年昊昊,他拥抱着自己的妈妈由衷地说:“妈妈,谢谢您。这些年,您辛苦了。”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1月11日,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这一场温暖的大聚会上,一百多名安装了人工耳蜗的“蜗友”和家人相聚在一起,分享走出无声世界的历程,共贺新年,也互相打气,携手前行。 当天,听觉言语康复专家、耳科、听力学专家为蜗友还会送上了科普课程,送出了40个免费耳聋基因检测和30个免费耳蜗调机。

这场2020年“寻声者”蜗友联谊会由长期致力于人工耳蜗研究、为听障人士谋求公益援助的珠江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张宏征教授一手操办。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欢声、父母们的欣慰动情,张宏征也“不争气”地滴下热泪:“他们经历了很多挫折,付出了很多心酸和努力才能做到正常人轻易能够做到的事,我很开心能够帮到他们。也希望以后有更多人一起来当‘寻声者’。”

分享一:失聪40年后,她第一次听见儿子喊“妈妈”
叶阿姨是在儿子和儿媳的陪同下来到寻声者大家庭的聚会的。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叶阿姨的儿子终于实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愿望——让丧失听力近40年的母亲,第一次亲耳听见了自己喊她一声“妈妈”。
“这是我成年以来所有干劲的最大来源。”陈先生说。叶阿姨在自己12岁的那年,某次双耳进水后开始出现耳痛、耳鸣,听力不断下降至全聋。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她从此生活在漫长的无声岁月中,从成长到结婚生子。也因为这样,她几乎长年都待在家中,默默操持家务、带孩子,很少外出。
“我从懂事开始,就知道妈妈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她听不见,但她给我的爱,丝毫不比别的妈妈爱孩子少。我真的很希望能让她再听得见我叫一声妈。这也是我长大以后做一切事情最大的动力。”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他也要拼尽全力帮助母亲重新听见这个世界。
十几年来,陈先生带着叶阿姨辗转多家医院,甚至两度尝试过手术,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后来来到珠江医院,找到张宏征教授。
张宏征说,叶阿姨的手术确实非常困难,因为长期失聪,双侧耳蜗严重骨化,造成人工耳蜗手术中难以获得插入电极的内耳腔道,这也是此前两次手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此外,近40年超长期听觉剥夺后是否能重新获得听觉,这是全世界的难题,即使冒各种风险成功完成植入了人工耳蜗,能否如愿听见声音,谁也无法保证。
面对这样的风险,还值不值得拼一拼?“我跟他们反复沟通过,一起决定一试。但我知道,这次如果再失败,对他们,对我来说,都会是一次严重的挫败。”
经过充分的术前讨论与准备,去年7月17日,叶女士的人工耳蜗植入术如期进行。张宏征教授需要在严重骨化的耳蜗内,用显微电钻一点点磨出一个小通道,准确定位残存神经末梢的位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偏半毫米,残存的一点希望可能就瞬间烟消云散了。”
所幸,手术成功了。术后3周,人工耳蜗开机,听到声音了!沉积在儿子心中三十年的遗憾,终于消散。
如今,经过不断调机、磨合,叶女士已逐渐能与家人进行简单交流。11日,在记者面前的叶阿姨依然言语不多,显得有些拘谨。但儿媳妇却说,她只是不适应从多年的无声一下子回到噪杂的环境,私下她最爱跟自己的姐姐讲家乡增城话,还爱跟亲戚朋友打麻将。在结束了访谈之后,叶阿姨雀跃起身跟大家道别的愉快申请,恰恰“泄漏”了她恬静外表下外向的一面。

分享二:恰同学少年,寻回声音勇敢前行
为了11日的分享,初二男生昊昊手写了整整三页的手稿。大声地读出了自己的故事和心情。当他最后和妈妈相拥着说“您辛苦了”的时候,张宏征感动地在一旁默默擦眼睛。15岁的昊昊目前在海珠区一所中学读初二。长期带着助听器,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什么“酷炫”的耳机,觉得这孩子“酷酷”地跟世界保持距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有身边最亲密的人知道,为了保持综合年级前一百名、物理年级前20名以内的水准,他比普通孩子付出了更多更艰辛的努力。但他自己却把这一切,当成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磨练,而“刷题”对他来说,也成了一种爱好。记者眼前讲述故事的昊昊,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
2004年6月,昊昊出生在天津一家县城医院。3岁多,别人家的孩子已经能说会道,小昊昊却只能眼看着妈妈的嘴唇蠕动,不知如何回应。那个时候,大人们还觉得可能是男孩子说话晚。长到5岁,才被确诊为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和感音神经性聋,开始了双耳佩戴助听器的岁月。
“我从未因为听力缺陷而自卑,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给我讲张海迪和海伦的故事,每每读到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就感觉我是幸运的,要更加珍惜每一天。”昊昊分享说。在助听器的帮助下,随父母来到广州生活的小学生昊昊保持着不错的成绩。直到初中,渐渐又开始感觉到听课吃力——“同学可以边听边做笔记,我却不行,总是听不清,课后总要花加倍的时间来复习才能跟上节奏。我听不清,只能去问旁边同学。我知道,谁也不可能拿着麦克风在大街上对我说话,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自行了解关于听力障碍的各种知识和信息。
直到初二,紧张的学业压力让他病情复发加重,头晕得走路都要摔倒,左耳没了听力,他第四次住进了医院,也第一次开始接触人工耳蜗。
家里经济条件一般, 30多万元的手术和机器费用,让人为难。“那段日子,爸爸为了我换了一份很累的工作;妈妈每天下班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打电话借钱,看到她为我焦虑、憔悴、苍老,我心酸极了。有一次忍不住了哭着跑过去跟她说:“妈,实在不行就不做了,就是穷也不能被别人看不起啊!”
倔强的少年变得自卑、愧疚,不敢向妈妈暴露内心对重新听见声音的渴望。那段时间,他经常发信心向张宏征诉说自己的苦恼。
张宏征也为他想了各种办法,提供帮助。2018年端午节的最后一天,张宏征带来一个好消息——他筹建的“寻声者”公益基金为昊昊找到了资助,可以手术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惊呆了,妈妈也哭了。这就仿佛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得到的一缕阳光,让我在最低谷重拾信心。”不久,他顺利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开机后听到妈妈声音的那一刻,我太开心了。为了尽快适应,我加强了康复训练,第三天就可以听音乐和BBC了。”
昊昊说,他从小就有个理想,希望将来能从事生物学医学或物理学方面的职业,甚至希望能够成为张宏征的学生。而且他要好好工作,多赚钱做慈善,帮助更多像自己一样的孩子,让他们本该快乐的童年,不再经历痛苦无助的折磨。“现在,我向着我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我相信终有一天必将践行!”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周洁莹 通讯员伍晓丹
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周洁莹 通讯员伍晓丹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吴婉虹
(全文链接:https://pc.gzdaily.cn/amucsite/pad/index.html#/detail/1120932?site4)